1860年9月20日,叔本华在起床时不慎摔倒,头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,但他看上去似乎并无大碍,当天晚上依然安稳入睡。第二天叔本华照常早起,仍按之前的惯例,洗完冷水澡后才吃早餐。女仆为他打开房间的窗户,让清新的空气流进来,然后才出门出去迎接医生。几分钟后,当他们走进房间时,发现哲学家倒在沙发的一角,已经与世长辞了。
人们在叔本华的遗稿中发现这样的文字:
“我一直都希望死得轻松……我将怀着已经完成自身的使命,为回归于那赋予我如此之高天资的来处而感到满心喜悦。”
在旁人看来,叔本华活得似乎并不成功而且还充满着痛苦。他幼年时就过上举家漂泊的日子,父亲的自杀更使生活蒙上了阴影;他患有多年的郁抑症,哲学作品不被世人认可,是无名的滞销书作家;在柏林讲学时还惨败给了黑格尔;他因不堪噪音干扰而将一名老妇推出房门,致其受伤,被迫打了6年的官司,最终败诉,成为人生的污点;他与自己的母亲反目,至死不相往来。在妹妹和卷毛狗相继离世后,孤独的哲学家才着手写作《附录与补遗》,如果没有这本书,叔本华或许还无法享受到人生最后9年的尊荣,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死去。
尽管一生充满着痛苦,但在叔本华看来,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能够带来愉悦的心情奔赴死亡,而不是像俗人那样满怀疑惑并略微不舍的离去——因为,叔本华能够直面生活的痛苦,看透了人生。

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
悲观的哲学,积极的态度
伏尔泰在哲理小说《老实人》中描绘了一个名叫邦葛罗的哲学老师,他逢人便讲“天下事有果必有因”、“事无大小,皆系定数”,又说“这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”、“万物既皆有归宿,此归宿必然是完美的”。他就凭着这套理论去生活,结果在吃尽苦头之后,才明白人生有三大忧患:烦闷、纵欲和饥寒。这个世界并非十全十美,人生的归宿也不是幸福,大部分人都只是平平淡淡、在枯燥无味的工作中过完这一生。
《老实人》实际是在讽刺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学说,邦葛罗这头蠢驴一味乐观,硬把坏事说成好事,他遭遇飓风、破船和地震,却还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灾祸就无法显示自己幸免于难的好运;他安慰老实人说,要不是被逐出王宫、遭受刑罚乃至流放美洲、弄丢黄金,大家就不能在农村里吃到美味的花生和糖渍的佛手了。明明自己被生活和贵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,还一味的搞精神胜利法,相信这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,这种乐观主义实在是自欺欺人。
叔本华也反对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,莱布尼兹认为不幸是一种消极的因素,它阻碍着人生的前进,生活就是要对不幸进行克服与否定。他说“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”,幸福的果实挂满头顶,只待我们去采摘。
对此,叔本华却说:
“莱布尼兹竭力维护这种荒谬观点,他企图用显而易见而又毫无价值的诡辩来加强他的论点。幸运恰恰才是消极的,换句话说,幸福和满足总是隐含某种欲望的实现,即某种痛苦结束的状态。”
在叔本华看来,不幸才是常态,而幸福则是不幸的短暂克服。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,快乐与满足是那么的短暂,更多的时候是枯燥、烦心与无聊。生活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幸福,而是“工作、忧虑、劳动和烦恼”。
谁不肯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,不肯面对大众所共同得到的经验,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够真诚。建立在善意谎言之上的乐观主义,除了自欺欺人之外,又能有什么积极意义呢?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悲观论倒是积极的,因为它敢于正视人生。只有丢弃“瞒”和“骗”的陋习,才能为生活寻出一条正路来。

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嘲讽盲目的乐观主义
痛苦才是生活的基调
在叔本华看来,人不过是生存意欲的客体化,是欲望的化身。七情六欲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,总是在匮乏与满足之间轮回,且匮乏的时候多,满足的时候少。不幸就像月缺,幸福则如月圆。
追求幸福就需要付出努力,而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辛苦乃至痛苦,此时的过程就像上弦月一样,逐渐向满月靠近;在欲望得到短暂的满足之后,无聊也就随之而来,月亮开始往下弦变化。
努力的痛苦多因匮乏,无聊的痛苦则因厌倦。前者通过千方百计的积蓄来满足内心的贪欲,后者却要进行肆意的挥霍,以免情绪变得抑郁。叔本华说“厌倦是痛苦的一种形式”,只有人类才能感受到它。对于那些多愁善感的富人来说,他们的痛苦哪里会比乞丐少呢?故而穷人节衣缩食、存储货币,富人则纸醉金迷、百般挑剔——谁都遭受了生存意欲的奴役。
推动人生向前的不是幸福与满足,而是不幸与痛苦。况且人生并非一直向上发展,对于个体来说,中年之前是上升阶段,晚年则走向衰亡。如果一个人活到了暮年,不顾躯体的衰退,仍要去追求所谓的满足与幸福,那会是多么荒谬的事啊。
可见,追求幸福并非人生中一以贯之的目的,人生的基调是痛苦的,我们所要做的是直面各个阶段的痛苦。
为什么要正视人生的痛苦?
人是生存意欲的化身,欲望只单纯地追求满足,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误观点——“来到这一世界,目的就是要过得幸福愉快”。
谁要是坚信这个错误的原则,就必然要被生活所捉弄了,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矛盾,处处与自己作对,剥夺了自己应得的幸福。当我们走出父母营造的温室,初次体会到生活的坚辛后,就会明白这一世界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幸福而设计。
当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,乐观主义者时而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环境,时而又归咎于别人,要么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,要么就责怪自己蠢笨无能。如果他肯放开眼界、审视人类,就会看到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幸的,很少有人能做到心满意足。大家在生活中都备尝辛酸,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,只得选择了苟且——如果人生的目的就是过得幸福愉快的话,那么未免也太虚幻了,因为人类的大多数都与它无缘。
真正说来,人们所普遍共有的应是痛苦。快乐的理由不胜枚举,而痛苦的原因无非是匮乏与厌倦。在人生的上坡路上,我们要直面痛苦,在匮乏与厌倦之间寻得平衡,避免滑向两个极端。这时候,我们是顺着生存意欲来行动的,我们要伺候好这个人生的主子,避免被它折磨;而到了晚年,我们的器官逐渐衰退,眼睛变花而五色衰,耳朵转背而五音退,牙齿脱落、味觉变淡,手脚日渐迟钝,记忆力也下降,而男女之欲更是消散。随着感官的衰退,生存意欲的锁链也变得松懈了。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转过身来,背对痛苦,逆着生存意欲,以此来净化人生。

在痛苦中净化我们的人生
人生犹如一片苦海,我们夹杂着泪水来到了人间,在生活的海洋中遨游,只愿到达彼岸。许多人不肯正视游泳的坚辛,不愿承认生活的劳累与痛苦,便拼命给自己幻想一个美好的彼岸来。他们编造谎言,对旁人说上了岸就是无忧无虑的天国,那里的幸福将会是永久的,不需要用努力和痛苦来做代价——他们不知道,在苦海的彼岸,等待着的只是死亡与虚无。
对于这个彼岸,叔本华说:
“死亡的确被视为生活的真正目的:在死亡的瞬间,一切都有了定夺,而之前的整个一生只是为此定夺而做的准备功夫而已。”
死亡就是人生的结果,是生活所结出来的果实,是对以往的一切进行定夺与概括。死亡告诉每个将死之人这样一个真理:人的一生充满着痛苦,不幸便是它的常态,然而你从来就不敢正视它。反而通过各种“瞒”和“骗”来安慰自己——你追求功名,一心往上爬,然而所有的帝王将相不都同为枯骨了么?你敛金聚宝,厌多恨少,然而要上岸时又有什么能带走呢?
死亡给你的人生做出了评判,你活了一辈子都没活明白,不知道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
只有当你在苦海之中回头观望时,才是一种解救和解脱。我们这一生有着无数次回头的机会,只是生存意欲统领着七情六欲,干扰了我们的判断。只有到了老年时,随着身体的衰败,意欲也会随之消退,就像傍晚的阳光不再刺眼一样,此时只要肯回头,便能看清生存意欲的真面目。

叔本华的哲学深受《奥义书》的影响
老年使人仿佛回复到生殖系统尚未发育前的无邪状态,这时自私自利让位给了对子女的爱、努力赚钱让位给了保持健康、奔波劳累让位给了享受生活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背对着痛苦,回过头去观看人生的苦海。看透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后,我们不再留恋与它,不再渴望永久占有。对幸福和愉悦的虚幻追求逐渐转化为安乐与沉静,人的内心不再苦于逐求、不再耽于贪欲,不必去为名利而勾心斗角,不用因为异见而口诛笔伐。
到了人生的末期,我们更需要做回纯粹的自己,获得了道德净化的契机。当我们日渐接近于死亡的彼岸时,良心的拷问会不时出现:我这辈子有过哪些不义行为?我伤害过了哪些人?我是否因自私自利而忽略了作公民的责任?如果我们做不到问心无愧,是否需要进行弥补,以免此生有缺憾?
当我们回过了头,把苦海人生都看透之后,心灵才会得到净化,并且在安乐与沉静中过完余下的日子,不再迷恋于长生,也不会悲观厌世,而是淡然处之。生活的痛苦依然会存在,但它已经不是我所要极力避免的灾难,而是像烦人的闹铃一样时刻提醒着——
我还活着,切勿睡去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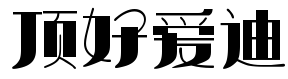 顶好爱迪
顶好爱迪




